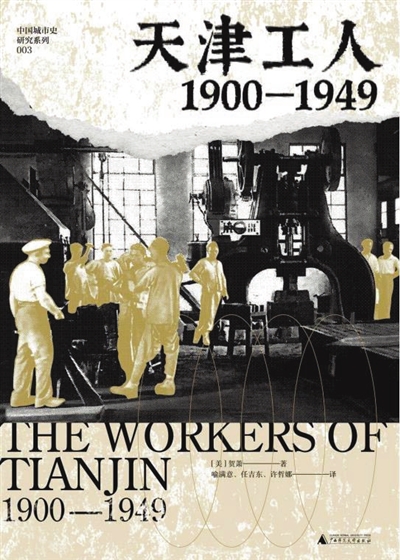
《天津工人:1900—1949》,【美】贺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诸多数据表明,近代中国工业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取得了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在空间上却严重失衡,集中在上海等主流工业城市。工业史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对尚未真正工业化城市的研究寥寥无几。作为最早一批到中国留学的学者,贺萧认为研究早期天津这样的“非工业化”城市,更能在新旧关系的过渡状态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并更易发掘人的具体命运。于是,贺萧在南开大学留学期间完成了《天津工人:1900—1949》。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史的重要考察内容,更是群体社会生活史的一部分。
《天津工人》宏观上以近代工业发展为主线,微观上从劳动雇佣、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织就一张近代天津生活繁荣全景网络,再现天津城市化进程。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着重于介绍天津工业的历史背景、投资情况以及工人的工作状况,直接将话题引入社会史范畴;第二部分用三个个案考察了机器制造业、运输业、纺织业工人的实际情况,揭示出不同行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如何应对生活以及对时局的反映;第三部分则揭示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及抗议罢工的情况。三部分中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环境影响了工作条件,也催生了不同的行为,潜移默化地熔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本书为人们展示了一幅近代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立足于大量一手资料或访谈录、报刊记录、回忆录等,读起来生动形象,也富有“人情味”。
贺萧再现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实际情况,“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影响而发展缓慢,一直处于试验性和蹒跚不前的状态”,虽然外国人控制了天津口岸,但除日本占领天津后的经略外,外资几乎没有对天津工业进行投资。天津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天津的近代工业在官方的微弱支持下缓慢形成,各方势力都对工业投资缺乏兴趣,每遇时局动荡,就要面临停产或裁员。而苛捐杂税、长期战乱、外部竞争、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等原因又阻碍了工业市场的发展,本土的工业产业顺其自然地成了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也仅是昙花一现,客观决定了近代天津工人地位低下也难有作为。
《天津工人》真切描述出工人群体的生活图景,1900年至1949年的天津工人在生产资料上几乎无所占用,靠劳动力赚取报酬勉强维生,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剥削,毫无致富的可能,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只会越来越贫困。从贺萧的记录看, 工人们的食物仅仅是勉强充饥,服饰仅够遮体,卫生状况极差,饱受疾病之苦,更谈不上什么像样的文化消费。多数工人因为收入低而频繁更换工作,情况往往不容乐观,却随时可能变为更苦难的底层。在这方面,天津的工人群体与中国多数工人阶级境遇相同,也与马恩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天津早期工业化之所以缓慢,在贺萧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天津的大型工厂,表面上看是机械化和‘现代’的,实际上却是在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基于旧式社会关系的管理体系下运行”。在几种工厂类型中,我们发现,其一,天津没有正式的行会组织,工厂主不能保护自身权宜,工人也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诉求。工人会受工厂主剥削,还要受到其他社会势力介入盘剥,而阻碍了现代意义上劳务契约关系的形成。其二,天津工业缺乏明确的劳动力分工,多数工厂采取了“熟人担保”式的管理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下工人流动率高,也是典型的“前工业”状态。其三,天津近代工人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进入工厂后,乡里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叠加,出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网络,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农村更封闭。这样,就形成了结构上既稳定又松散,关系上既传统又开放的矛盾体,极大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也是造成天津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直接原因。直至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真正扭转。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贺萧发现,近代天津工人阶级没有完全转变为工人无产阶级,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只能开展零星的斗争,面对与工厂主的矛盾他们只能投机取巧。贫穷和压迫导致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但他们的罢工不是因为阶级意识的觉悟,相反仅维持现状就足以平息工人们的怒火。帮会、工会或者其他中间势力无力发动影响深远的罢工抗议,工人们处于“碎片化”的分割状态,阶级阶层结构不稳定且地位低下,劳动状态处于密集型的底层,加上生活环境差、文化品位低等因素,按照卡兹尼尔森所设定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四层次(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来审视,新生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传统形式无法平衡,这样的情形在20世纪上半叶长期存在。而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开创翻天覆地的工人运动新篇章。
贺萧从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与同时代中国学者从政治传统角度作出的研究截然不同,开启中国“生活史”“新工人史”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汉学者,贺萧面对异国文化也存在过度的惊异。此外,本书还对诸多常识性结论展开论述,大费周章,这些都反映出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认知错位。
贺萧主张从边缘看核心,从外围看整体,最典型的就是将近代家庭作为经济共同体与生存单元,工人家庭人人需要工作,都处于高压状态下,异常艰难。特别是为降低劳动成本,工厂出现了女工、童工等弱势群体,这是作者特别关注的部分。宏大的政治历史研究极易忽视工人内部的差异性,而贺萧恰好关注到工人在性别、年龄、籍贯、社会关系、技术程度等因素的区别,她以收入、消费、文化等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立足个体化的“小叙事”,打破了传统劳工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即便口述史、回忆录具有情感成分,但作为生活史的一部分仍成为令人信服的论据。
最后,贺萧反驳了汤普森(英国工人史、文化史学者)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彼此利益一致”的观点,天津工人置身于众多社会关系之中,他们似乎没有“共同经历”,也不曾“利益一致”。贺萧对结构化的社会形态存疑,她曾提出,“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个纯正的阶级样本”。因为生活的变动,工人内部必然形态各异。《天津工人》中大量的材料呈现出工人阶级各异的日常点滴,能动性与主体性跃然纸上,揭示出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倾向。贺萧着眼于工人本身的行为动机,其历史选择可能与既定的时代主旨不符,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贺萧撰史的思路,即汤普森所提倡的“人民的历史”。
附件:


亲爱的朋友: 经系统检测,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为了改善你的体验,请升级新版IE11,新版EDGE,Chrome,火狐等浏览器。点击此处升级

分享到: